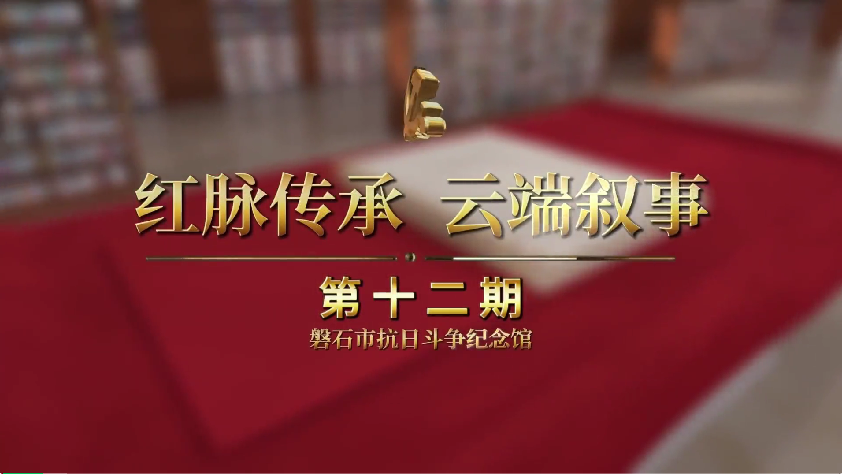
在吉林省博物院的玻璃展柜里,这把锈迹斑斑的铁铸单刀静静躺着。67厘米的刀身刻满岁月的痕迹,刀柄缠着的蓝布虽已碳化,却依然保留着铁血少年的体温。当灯光掠过刀背模糊的刻痕,你可知道,这把国家一级文物的主人,曾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15岁的“铁血少年”?
1931年“九一八”的炮声震碎了东北的宁静,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让白山黑水迅速沦陷。但就在这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上,杨靖宇组建了一支特殊的队伍——铁血少年营。这群13到18岁的儿童团员们放下课本,拿起单刀和长矛,在磐石抗联密营里用雪水淬火打磨刀刃。据史料记载,这支队伍不仅能站岗放哨、传递情报,更在老岭隧道、长岗等战役中“歼敌数十人,收编百余人”,把日军打得闻风丧胆。
刀鞘里半片碳化的桦树皮上,至今能辨认出模糊的刻痕:“1933年12月15日,墙缝沟。”那天,400多名日军将少年营包围在磐石北部的山谷里。17岁的刘福臣把这把单刀插进雪地,对战友们高喊:“你们快撤,我枪准!”他和营长陈玉振背靠背阻击敌人,刀光在零下30度的风雪中翻飞,直到最后一颗子弹耗尽。刘福臣牺牲时,单刀还深深嵌在敌兵的胸膛里,而他留下的这把刀,刀身三道崩口正是当年砍断日军刺刀的印记。
这把刀见证过少年们用磐石二道沟的地形打游击,夏天钻苞米地设伏,冬天裹着破棉袄在雪窝潜伏;见证过他们把冻硬的苞米饼当干粮,在战斗间隙发展抗日力量;更见证过杨靖宇将军亲自给他们包扎伤口,用棉衣撕下的布片裹住刀柄说:“刀要握在活人手里,才能劈开亡国的黑夜。”1964年,当磐石农民在开荒时从1.2米深的土里挖出它,刀鞘正朝向东边的抗联密营遗址,仿佛还在等待少年们归来的脚步。
如今,刀鞘内侧未写完的“胜”字依然清晰,那是少年们没来得及看见的胜利黎明。当我们抚摸展柜的玻璃,可曾感到:这把刀不是铁铸的,是东北少年的脊梁锻成的;刀柄缠着的不是布条,是永不熄灭的民族精魂。锈迹里的每一颗铁分子都在诉说:少年不屈,则中国永远有刀刃劈开黑暗的力量;这把单刀刻下的,正是一个民族在风雪中挺直的——少年中国。